文库/小说/抵御疫情的屏障,也隔离了人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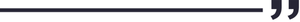
计程车从东门岗亭驶入校园,没走多远便被拦下。距离东门岗亭不远的地方,不知何时又矗立起一座岗亭。乘客从车上走下来,计程车司机一脸懊恼。
“你是什么人,来学校做什么?”乘客走到岗亭面前,值班人员盘问道。“学生,今天返校。”“刷一下学生卡。”值班人员指了指旁边的机器。一声清脆的“啪嗒”,是学生卡拍在机器上的响声。“请通行”,机器发出声音。“出租车不能进,拿好行李走进去。”“啊?!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麻烦……”学生拖着两个很大的旅行箱,嘟囔着。
这只是北关大学纷繁复杂的防疫措施的冰山一角。从疫情常态化防控以来,在大学求学的学生似乎只感到越来越多的不便。
1/7
25年,我从老家来到丹桂,在北关大学做一名保安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大学的保安并不是什么苦差,每天的任务仅仅是在岗亭值班,或者在教学楼查学生们的证件,至于骑着电摩在校园内巡查的任务,有固定的人手来完成。
就在我以为一切就这样了的时候,一切都天翻地覆。26年,一场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国,弄得人心惶惶。学校出台了封闭管理的命令,我们大年初二就收到了返校上班的通知。好好的春节假期一天不剩,保卫处的同事们心里都很烦躁。
接下来的日子和去年天壤之别。学校在家属区和教学区之间新设了四个卡点,除去教职工一律不得进出。而我们就负责看守这些卡点,不让任何一个人违反学校的命令。这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,同事们一个个累得龇牙咧嘴。
由于岗位突然变多,人手不足,我们必须每天两班倒,一班12个小时。在保卫处休息的时候还要值班,巡逻队员每天轮换。睡眠不足成了常态,我们在保卫处里面找了一个房间,铺上几张床,算是临时休息室。
每天熙熙攘攘的人出入校门,想控制住漏网之鱼谈何容易。天津确诊人数最多的那一星期,我们平均每天都要拦下7个到8个试图混入学校的校外人员。一开始我们是劝他们离开,大多数人还是听话的。但遇到难缠的人也很麻烦,你跟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。就在4月份武汉刚解封的时候,有人闹事想冲进学校,被我们班长拦下之后一边骂一边试图把我们的设备砸掉,我们当班的四个人都来控制他,最后五个人打在一起。班长被砸破了头,所幸没有缝针,不然他可能一时半会都不能来站岗了。
更多的麻烦是校内交通上的。疫情以前学校不收停车费,所以到了早晚高峰会有很多社会车辆为躲避堵车选择穿行校内。封闭管理刚开始时,每当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,因为总有一些私家车会从东门旁若无人地开到我们面前,按喇叭要我们放行。我们还得费半天劲解释为什么学校不能穿行了,毕竟大家遇到这种封闭管理政策,多少有些不服气。后来我们直接放了一个牌子在大门外,写着“去西南村、西门方向请绕行复康路、白堤路”,这之后要求穿行的私家车明显变少了。
学校的三个家属区分布在西边、东边和南边,平时靠校内道路连通。校园封闭管理的同时也带来了家属区的不便。有很多老人需要见亲友、去西南村买菜、或者去银行办业务,他们还希望从校内穿行。后来我们把这事报给学校,学校很快下达了政策:校内离退休人员可凭退休证进校,无需绕行校外。这样老人们就能够在校内交通压力相对小的道路通行,更加安全和方便。
2/7
要开学了,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分年级分批返校。首先是毕业年级要回来参加答辩之类的,领导特意给我们开了一个会,强调了接下来的工作。我们校区这批毕业生大概有3000人,返校程序一旦开始,就势必给防疫增加压力,所以我们必须拿出十二分的警惕来,把常态化防疫工作按部就班地推进,确保零失误。开完会之后,学校又往保卫处抽调了10名防疫员,看来这是一场大仗。
疫情趋于好转,为了迎接学生返校,新的出入管理政策在留校的学生身上做起了试验。每个卡点配了两台POS机一样的设备,一台负责出校,一台负责入校。学校允许学生每天0:00-24:00不限次出校,在外过夜的学生会被禁止入校。试行以来,保卫处的各个部门都反馈良好,唯一的缺点就是学生们还不适应出入校刷卡的管理方式,总是需要我们去提醒。在学生批量返校之前,保卫处又做了一个“学生出校主动打卡”的牌子立在各个卡点醒目的位置,后来忘记刷卡的学生普遍变少了。
5月各行各业都在恢复生机,而外卖电动车也开始飞奔在大街小巷。据说外卖行业刚刚恢复的那段时间里,平均每天有500多单外卖的目的地是北关大学校内。送外卖的电动车一辆接一辆地被拦在我们面前,骑车人望着进不去的校内满眼焦灼,一遍又一遍地通知买家前来取餐。外卖人每天在马路上不顾一切地穿行,在这校门口等待的时间,或许足够他再接五六单。匆匆忙忙地,睡眼惺忪的男生女生披着外套跑到栅栏门,一份份外卖跨过栅栏送到他们手中。在这种情况下,会不会有人做起“代取外卖”的生意呢?或许会吧。
夏天到了,校外的生活似乎和疫情前没有什么两样。除去公共场所的常态化管控措施,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看不到口罩的身影。端午假期人们开始出游,各大公园熙熙攘攘。即将迎接返校学生的校园却是丝毫不敢放松。成千上万人的校园,一旦疏于管控,后果不堪设想。为此我们保卫处人更是加劲奋战。人手不足,超时工作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,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,没有休息日,但大家支持并理解学校的决策。有时同事们还会和我吐槽一下防疫政策下的工作辛苦,但一想到在这样的规则下大家都能平平安安,我们就感到一切值得。
返校的日子来了,市里非常重视,给学校配了十辆崭新的公共汽车,还是两节的。每天都有许多学生拎着大包小包来返校,我们也会督促他们刷卡。偶尔有想不排队直接往里进的,也被我们一一劝阻。比起爱好打架的校外人员来说,大学生显得文明许多。
随着外界的秩序逐渐恢复,学校的出入管理难度也在上升。保卫处每天至少有6个人在监控室值班,盯着校园内的每一个角落,防范着乘人不备混入校园的外来者。就算这样,还有一些骑着电动车的人肆无忌惮闯入学校。我们无法追上他们,就用对讲机联系巡逻人员阻截。随着在校人数的上升,巡逻队的规模扩张了一倍。
3/7
魏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,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场新冠疫情会使生活变成这样。授课改成线上,开学遥遥无期。在家里憋坏了的他开始寻找各种出门的理由。他无数次在户外偷偷摘掉口罩,他渴望回到与口罩无缘的生活。
结合大数据、互联网技术,各地都迅速地推出了“健康码”,不同的颜色代表此人是否与疫情风险地区或人员相关。魏聪原本以为防疫措施就是这样简单方便,直到2月6日,学校上线了防疫填报系统。系统要求学生每日填写一次,细节包括体温、所在地、相关症状等。初期,魏聪每天都在认真地使用体温计,仔细核对每一个填报项,而过了一段时间,魏聪实在是受不了每天机械性地重复这种动作了:本来就闲不下来,还要浪费时间测量体温吗?水银体温计就放在床头,一不留神碰掉了怎么办?每天都在家,为什么还要填写相同的地点?我明明哪也没去过,怎么会接触到和风险地区相关的人?全国联网的健康码,不能证明我的健康状况吗?越来越冗长的表单,让魏聪开始怀疑这样的防疫是否有意义。
魏聪开始愈发反感这个防疫填报系统,从一开始的认真填报,到后来的漫不经心,再后来直接屏蔽了消息中心的提醒。但是防疫填报系统是不得不填报的,因为一旦忘记,辅导员的电话就会打到手机上,甚至是家长那里。在经历了辅导员的数次电话提醒后,魏聪发现消极抵抗不是办法,索性随便编个体温,反正自己已经一年没生过病了,最近也没什么异常。重新打开消息提醒,每天起个大早填报,最后魏聪愣是让自己6点起床一次,8点再起床一次。由于学院要求防疫填报在12点前完成,魏聪到了假期连懒觉都不敢再睡。但魏聪始终心里有个结:我这样做,究竟是为了什么?这样防疫防得住无症状者吗?这样防疫会不会有人瞒报、乱报?如果这样防疫有效的话,为什么隔壁丹桂大学没有这种东西?
5月初,魏聪突然收到一条提醒,要求全体学生改用飞书进行所有校园业务的处理,而微信公众号即将停止服务。看到这条消息,魏聪的第一想法是:“有必要吗?”大家已经习惯使用微信公众号这样的平台处理校园业务,如今却要从头开始,使用一个完全陌生的软件。打开应用市场,搜索飞书,高达500MB的体积让魏聪更加怀疑安装飞书的必要性。“装一个飞书,不就等于多了一个微信?只为那么几个功能,何必呢?”5月16日,微信公众号如期停止服务,而魏聪发现除了平台变了以外,防疫填报没有任何的改变,依旧是冗长的表单,不知道是否有效的选择题。魏聪不知道这样作息紊乱的生活几时结束,也不知道防疫填报在抗疫措施中究竟有多少贡献。
4/7
8月初,学院调查学生的返校时间,不了解情况的魏聪便填写了返校报到日——9月14日。可是随后魏聪便收到了班长的消息:报到日前一周有上学期期末考试,需要提前返校!云里雾里的魏聪把返校计划提前了一星期。8月中旬,魏聪在学院飞书里收到了排考的安排。上学期四门专业课的期末考试,以密集的方式安排在一周之中。“出来混,总是要还的啊。”上学期的知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的魏聪自嘲道。
8月25日,距离返校还有14天时,魏聪收到了学院的返校通知。未来14天里,他要每天截图健康码绿码,并签署一份返校申请书。魏聪看到申请书上面写着:“本人______,因______原因,现申请提前返校。”魏聪苦笑了一下:“没办法,成绩要紧嘛。”不巧,小区里的打印店老板因私事歇业,魏聪只好坐了好几站公交到镇上打印。看着申请书从打印机里慢慢冒头,魏聪找了支笔,在打印店就签字并且提交了材料。
魏聪是希北人,所以在9月5日,距离第一场考试还有3天时,他乘着高铁回到了学校。打车进入学校东门,不知道什么时候起,学校里立起两道岗哨,帐篷下的保安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经过的人。出租车被拦住,魏聪被保安喊下车。魏聪小心翼翼地向保安试探:“我是返校学生,能直接进吗?”“刷卡。”保安机械地重复着。魏聪将校园卡放在机器上,机器发出了“请通行”的声音。“走吧”,保安说。魏聪松了口气,想要开出租车门。“出租车不能进,拿着行李走进去。”“啊?我两个大箱子,还有别的啊!”魏聪立马泄了气。“没有办法,规定就是这样。”保安丝毫没有退让。魏聪懊恼地向司机支付了车费,推着两个大行李箱和一个装衣服的大包,踉踉跄跄走进学校。不过让魏聪感到些许慰藉的是,学校里面的交通车贴着“返校爱心车”的大字,上去一问不要车费。魏聪的大包小包终于到了宿舍,而此时,他的外地舍友都已到齐。
返校到考试的短短几天内,魏聪就全方位感受到了常态化防疫下,校园生活的不便。魏聪早晨起来,想吃个早饭,然后再去二主楼复习考试,结果三食堂限流,他在门口排了20分钟队。当他到达二主楼门口时已经快九点了。门口的保安向他要健康码绿码,魏聪更加疑惑:健康码和防疫填报到底什么关系,为什么不能整合在一起?戴着口罩学习,魏聪呼吸短促,总是分神,魏聪只好跑遍二主楼,找了个人少的教室,半掩口罩,勉勉强强学了一个小时。中午吃饭的人熙熙攘攘,二食堂又只开放了一楼,门口再次排起了长队,这次是半个小时。魏聪想打个球,却发现球场要提前预约,图书馆也是。晚上魏聪拿着用具去浴园,却被舍友告知浴园限量预约,需要抢名额。魏聪设了一个明早8点的闹铃用来抢浴园,自言自语道:还不如不返校呢。
5/7
在国家强有力的管控措施下,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,甚至与疫情前并无二致。国庆假期出游人数达6亿,绍虹火车站全国车票一夜售罄,如此声势被调侃为“迟到的春运”。在希北生活的魏聪,出入小区已不再需要任何证明。永宁寺门票预售后被一抢而空,各大景区熙熙攘攘,人比景致多。
但是学校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辅导员们在紧张地工作,认真申报每天学生的状态。保安们不分昼夜,校门的严格防控没有丝毫放松。返校审批、填报体温、出入刷卡依旧构成了学校抗疫工作的主旋律。而从家中回到学校的启龙,更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便。
截至26年12月4日,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人数65460111人,美国成为首个突破千万大关的国家,国内目前现存病例271人,11月9日丹桂太平洋生态城关联病例累计5人。如何在“后疫情时代”协调防疫与生活的关系,每所高校都交出了不同的答卷。而北关大学这一份试题,貌似有点长。
和多数大学生不同,学医的启龙有十分严重的洁癖,舍友邋遢的生活方式让他每次走进宿舍,都会感到胸闷心慌。启龙以为自己能够承受这样的环境,努力了一年融入集体生活。可是大二刚开学,启龙就感觉被宿舍生活扼住了喉咙,他的失眠日益加重,精神恍惚。本硕连读还有七年时间,如果不想想办法,他觉得自己肯定坚持不下去。
启龙给父母说了大三搬回八里台后想回家居住的想法,父母表示支持。他的家距离北关大学不算远,五公里左右。于是启龙和父母做好了详细的路线安排,期待着大三之后每天通勤的旅程,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更好的状态。可是谁也没预料到,就在庚子年的伊始,新冠病毒打了全国人民一个措手不及。一学期的网课后,启龙按照学院的安排准备返校事宜,其中就包括出入校的申请。启龙本以为在防疫措施完善的当下,学院会对自己网开一面,允许自己走读就学。可惜在启龙无数次保证做好防护的情况下,医学院强硬的辅导员还是开出了死命令:要么返校,要么走人。周旋失败,启龙只好抱怨着接受了这个设定。
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。谈判失败只好每天待在学校的启龙,开始寻找学校里各种可能的死角。启龙从谈恋爱的同学手中找到了一个秘密微信群,群里都是北关大学的同学。群里的同学每天都在寻找校园中任何可能的盲区,并分享给群里的其他人,好让大家成功“偷渡”到校外。群里的人越来越多,“偷渡”理由也五花八门,见朋友也好,见网友也好,见恋人也好,这个小群成了同学们最后的生命线,他们的群名叫“肖申克的救赎”,或许是对艰难境况的自嘲。不过在启龙看来,依旧在限制学生自由的学校,和肖申克监狱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6/7
为了无痕迹出入校园,同学们处心积虑寻找校园安保可能的漏洞,打起了游击。经济学院、西南村、东村北村,任何可供一人钻过的通道都是他们的绿色通道。与此同时,校园安保也在对校园的盲区不停地自查,对校园的围栏不断地修补升级。西南村菜市场的人行通道,刚开学时只是简单封堵,开学后不久便砌成了两人高的混凝土墙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一个通道被堵死,千万个通道被开辟。为了钻出学校,甚至有学生开始用老虎钳弯折校园的铁栅栏。那个被称为“肖申克的救赎”的小群,也逐渐沉寂下去,谁也不愿意把好不容易发现的通道再分享给其他同学。
无数“偷渡游击队”在校园游荡的生活,被某位同学在北村的一个惊人发现结束了。他们发现在无论校方还是学生都从未注意过的一个地方——北村的排水河中央,有一座拦河坝,两米宽,从西岸到东岸,两头落差一米左右,正好适合大家“偷渡”。不管这座坝为什么而建,里面是管线抑或水泵,也不管为什么校方这么久都没发现这里,所有“偷渡”的同学都涌向这座水坝,窄窄的水坝成了北关大学的“鹊桥”。得知这个消息的启龙自然也是欣喜万分,从这以后,他在母亲上班,没法接送的日子里,就坐运通106路,从家门口坐到八里台,再从北村的侧门来到这里。走在坝上,他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从这里出入校的同学,他不认识他们的脸,相视一笑,侧身而过。

学校依然在封堵着一切有可能出校的小路,唯独这里始终没有被校方发现。就在启龙以为这一切都将变得稳定的时候,出事了。
一个普通的星期五,启龙照常从拦河坝溜进学校。当他从校园一侧爬上来的时候,他发现事情不对。草坪上站着几个保安,巡逻的电动车停在后面小路上。启龙一下就懵了。“为什么要从这进来?你是校外人员吗?”“我……我是学生……我有学生卡,请你们别告诉辅导员……”启龙结结巴巴地说。他挥舞着自己的学生卡,试图证明自己的身份。但是这张用来出入学校所有场所的凭证,第一次失去了它的作用。“把学生卡给我拍一下,这个需要通知你们学院做记录。”“能不能不记录,因为我不是故意往校外跑的……”“不会影响你什么,就是登记一下。”保安给启龙吃定心丸,可启龙总是不放心,他怕他的辅导员再次因此事起意,针对他。
下午,启龙回到那个陪伴了他一个多月“偷渡”生活的拦河坝,只见拦河坝的校园一端已经挂上了六米宽的挡板,对岸还装上了监控。他没有想到,他梦中的鹊桥就这样顷刻间分崩离析。想起他的高中同学在学院辅导员的帮助下,每周申请出入校的权限,他说:“为什么我这么难啊……”有水珠滑过脸上,启龙舔了一下,很咸。
此一役,学校的“偷渡”出口算是彻底被消灭干净了。启龙每天翻过北村树林里的矮铁栏进入学校,羽绒服上全是痕迹。双臂越来越强壮的启龙,现在最希望的是学校不要再加高任何地方的围墙。
7/7
在疫情的影响下,疫情前的熟人社交几乎占据学生社交的全部。疫情之下人们会更亲近还是更疏离的问题,显然早已有了标准答案。疫情当下,校园里似乎处处都在引导年轻人做一个社恐者。戴上口罩,即便熟人见面也无法认出;食堂设置隔板,让拼桌的邂逅也成为历史;校区的封闭,让同学间的友谊渐渐稀释……有的人艰难地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,却发现十分困难。学生会也好,社团也好,真正能在一起说几句话的没有几个;而指望在课堂上展示自己,从而朋友广交的同学,也不得不面对同学们在半年中更加紧闭的心门。表白墙成了大家表达好感的平台,可是俗话说“闻名不如见面,见面胜似闻名”,又有多少人当着自己喜欢的人,把心中的那句诺言用水泥封印起来,仿佛它的泄露比核反应堆还要可怕。
而防疫过程中的“校门关”,似乎也并没有那么严格。十月底,一位同学被非要堵着岗亭进校的校外人员挑衅,还被撞坏了电动车,索要赔偿却被对方殴打。事情闹到派出所,警察来搜集证据,可是翻遍岗亭登记,也找不到校外人员进出的记录。原来学校的出入管理仅仅是对学生严苛而已!学生既要修车又挨了揍,校方“维护学生利益”的口号成了一句空谈。
住在校内的同学们,防疫填报被调整为在校模式,而这个模式只允许学生在11点至13点进行填报,返校前是0点到13点。十一点四十,专业课的期中考试结束了,同学们一边吐槽题目的困难,一边去食堂吃饭,他们用校园卡付款,直到回到宿舍才发现已经过了13点,只好给辅导员发健康码。在学院学生会权益部的工作档案上,写满了希望优化防疫填报时间的学生意见,但至今也未被实施。
跨两个校区双辅修的同学们,由于两校区出入境政策的差异,他们不得不在两个校区之间循环申请出入校,如果乘坐点对点公交进入丹南校园,甚至要回到校门口重新打卡,否则就会按晚归被取消在校状态。幸运的同学申请到了临时宿舍,不用再循环申请,可是他们的大脑必须时刻记住“我到底哪个校区还没刷卡?”这样没有意义的问题。
不仅是学生,教职工和家属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九月底,一群渴望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的师生们组织了一场广场舞,竟因为“给防疫造成压力”的原因被紧急叫停!后来经过大家的讨论,决定向校领导上报。好在最后问题得到了解决,学校特意派人划定了广场舞点位,广场舞总算没有被疫情抹杀。
常态化防疫的深入,在同学们的眼中,渐渐矫枉过正。虽然经历着防疫措施的大量冗余和低效,学生们却很少去思考防疫措施的合理性。或许在大家的眼中,复杂和多余的防疫措施意味着安全,而有效和高效并不是大家过多考虑的内容。
漆黑的夜,人影稀。不知是入夜太早还是天气太冷的缘故,本来应该热闹的湖边空无一人,没有谈坐的情侣,没有仰望星空的思考者,亦没有静坐歇息的路人。
北关大学的冬天,要来了。
